蔡磊背后,有个神秘的“国家脑库”
进了院子就看到两间平房,一间是会客、就餐的堂屋,另一间是卧室,每间房有十几平方米。
与屋外明媚的春光相比,屋内光线有些昏暗。部分墙皮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土砖。
因为疾病进展,郭先生说话有些口齿不清,但他比较健谈,招呼我们吃这个吃那个。郭先生的妻子则柔和、安静,一直在土灶边忙碌。
郭先生原本在筑路工程队做技术工作,2018年发病后很快失去劳动能力,只能回家。
随着病情进展,他“连裤子都提不上去了”,也没法做饭。在杭州打工的妻子便回来照顾他,夫妻俩都失去了收入来源。“我们还曾经存下一点钱。”妻子小声说。这种因病致贫在渐冻症患者家庭中很常见。
我们后来去他家拍纪录片,妻子穿着一件亮眼的橙黄色制服,郭先生很自豪地说那是他以前的工作服。因为轻便、防水,他就给了妻子,方便她上山干活。

·郭先生及妻子在家中,妻子穿的橙黄色制服是郭先生以前的工作服。
仙居是浙江有名的杨梅之乡,郭先生家也有杨梅树。当时正是杨梅成熟的季节,郭先生执意让他妻子摘回来一筐招待我们。
关于捐献,他的想法很朴素,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反正最后烧了也是烧了,一点价值都没有,多可惜!”
这次探望郭先生大约半年后,我在一个凌晨接到了他去世的消息。按理说他的病程只进展到中期,我没想到他会走得那么快……
在他去世后第三天,我终于联系上他女儿小郭。
她哭着告诉我:“最后爸爸的药都是我们找亲戚借钱买的,结果药还没吃完爸爸就走了,看见那些剩下的药瓶,我心里就难受。”
我这才知道英雄在生命的最后,经济上是多么窘迫——我们两次探访期间,他从未提起经济上的困难。

·2023年,刘华清(左)和志愿者去患者家探访,经患者同意后查看其病历。
20世纪80年代,美国科学家大卫·斯诺登开始酝酿著名的“修女研究”,目的是研究年龄增长与阿尔茨海默病的关系。
修道院的卡门修女愿意动员大家参与项目,但她同时也告诫大卫·斯诺登,不要把修女们仅仅当成研究的受试者:“我希望你真正地认识她们……不论你做什么,我都希望你记得这些人是谁。她们是真实的人,是我们爱的人……” 最终有678位修女加入研究,在去世后捐出了自己的大脑。
卡门修女的提醒,也是我联系渐冻症捐献者后的强烈感受。
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一个个在苦难中坚强的家庭。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文化水平和家庭背景,却因为对病友的共情和对科研的信任,在经历疾病残酷的折磨后,不约而同地选择用献出自己的方式反哺世界。
他们是那么平凡、朴实、坚韧、伟大!
“脑库的运作像一个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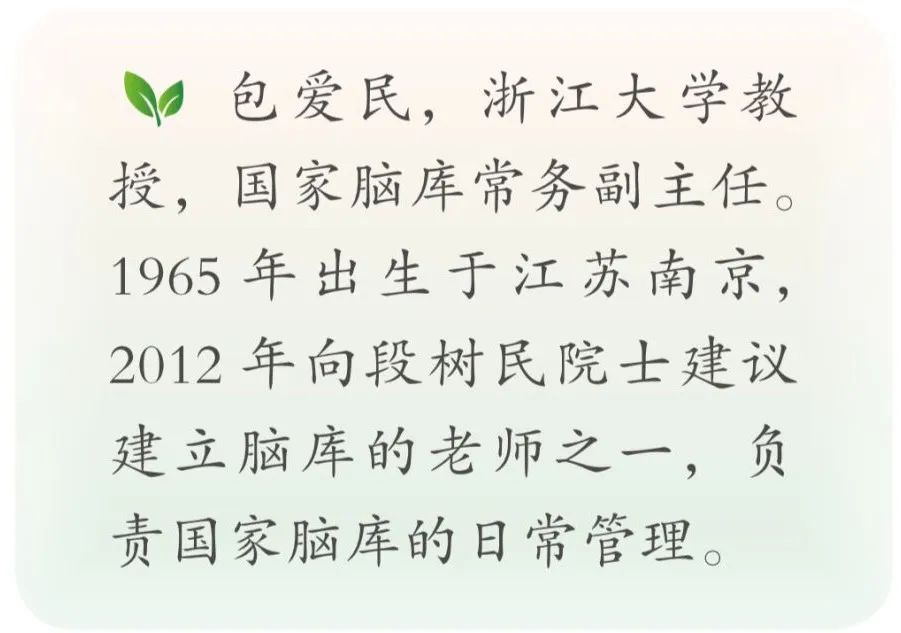
冰箱里的温度低至零下80摄氏度,必须戴着专用手套才能打开。
包爱民小心翼翼地拉开其中一层门,20个小盒子分格排列,每个盒子里装着不同脑区的“新鲜”冰冻样本。捐献时间、第几例大脑、分属脑区,都在盒子上标注清楚。24台大冰箱,可以储存600多例脑组织。
“但脑库一定不是为了存脑,最终的目标是向外发送,我存了多少不值得自豪。”包爱民自豪的是,国家脑库已经向国内90多个科研项目提供了9000多份研究样本。
以下为包爱民的讲述。
我们的核心工作分为收集、储存、发送3个核心环节。
首先是收集去世后的人脑组织。每次有大学生参观完国家脑库,都会说:“包老师,我也想捐献!”
我说:你得回家和爸妈商量商量。
所有捐献者都要签署《国家脑库捐赠者知情同意书》,同意书除了对标国际伦理规范外,还做了一些更贴心的设计。
比如,如果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捐赠者或者家属改变主意其登记信息和知情同意书可以撤销,无需说明理由;捐赠者声明除了本人生前签署之外,必须还有一位至亲家属签名。
当捐献者去世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把大脑取出,把遗容遗貌修复好,再将遗体送回殡仪馆或家里,一点也不影响遗体告别。

·国家脑库档案柜里整齐排列着一小盒一小盒的石蜡组织块。(雷迅 / 摄)
为了满足科学家不同的科研目标,取出的大脑通常分两半保存。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相当重要,我们必须保证最终的样本质量,这样才不辜负信任。像放冰箱的房间,是双电路供电的,可以保证一条电路停电,立马由另一条电路供电。
此外,我们必须做好“最后诊断”。不做最后诊断,其他都是徒劳。
比如,科学家想研究抑郁症病人,结果一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临床上被误诊为抑郁症了,如果我们根据生前诊断将脑样本发送给科学家,那研究结果大概率也是错的。
因此,就需要一名专业的病理师,像侦探一样,根据染色切片还原出人脑疾病准确的“案发现场”。

·2023年,包爱民在国家脑库办公室。
还有人问我:我的大脑很健康,是不是捐献了也没用?不是的。我们发送给科学家的人脑样本都是病例—对照样本,一个成熟的脑库,健康的大脑数量应该至少是带病大脑的4—5倍。
脑库的运作像一个银行。捐献者去世后把大脑存在银行里,大脑是他们的珍贵遗产。
科学家再向脑库申请人脑样本,最后产生的利息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认识,是治疗的方法,也是新的药物、人类的希望。
现在,因为兼顾国家脑库的工作,我的科研时间被挤压了很多,但我一点也不后悔。相反,我觉得目前是我最好的状态,毕竟你一个人做,顶天了能做到什么程度?科学的发展更需要一群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