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渐冻症专家樊东升:寻找长夜里那束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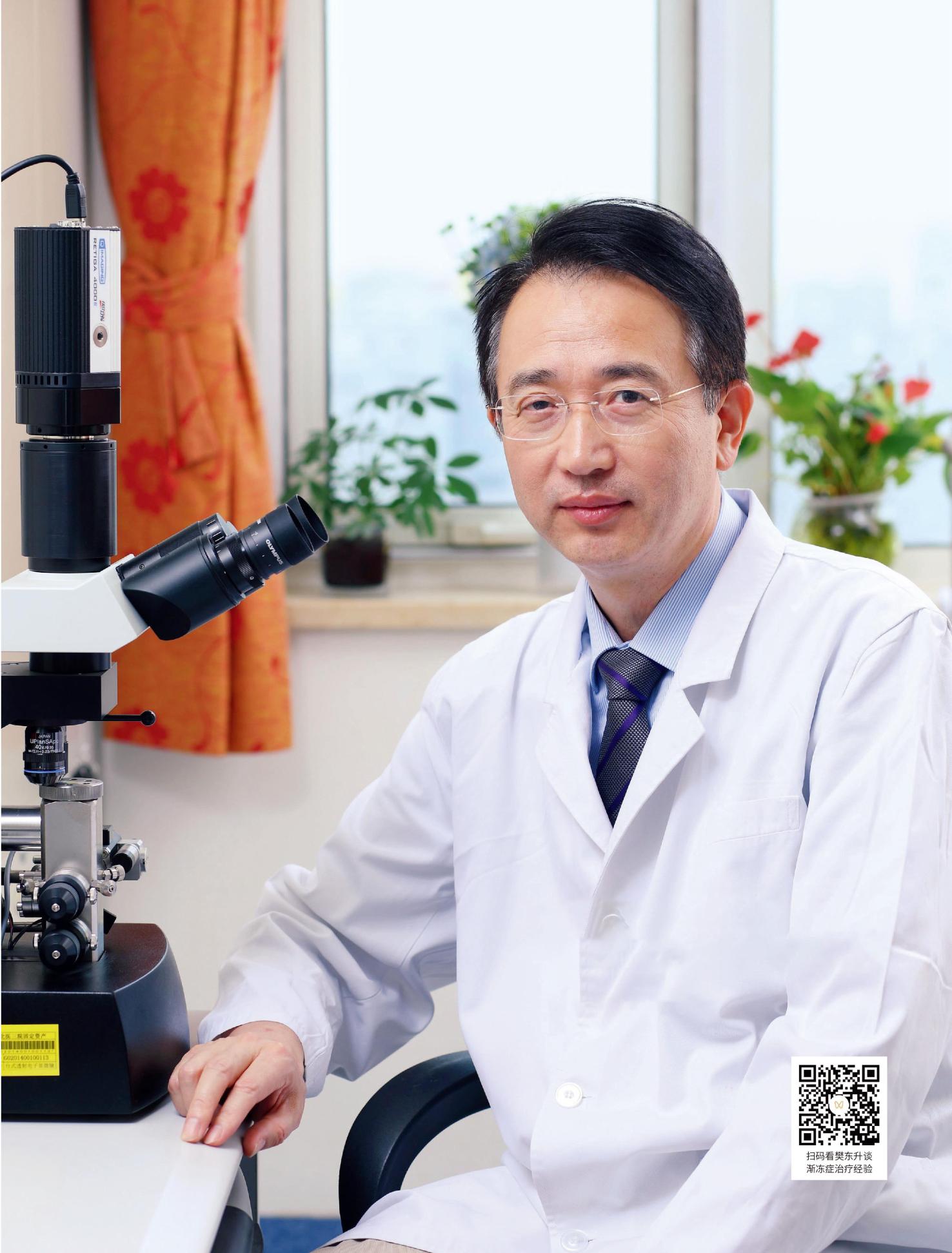
樊东升,蔡磊的确诊医生,数千名渐冻症患者的主治医生。1963年出生于山东济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学系主任。
找上樊东升,是很多患者不愿经历的事,这意味他们大概率将被“判刑”。蔡磊的书里就记录了自己确诊的过程——一名医生听完他半年多寻医问药的过程,很干脆地建议:“其他地方都不要去了,你就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找樊东升专家团队,看看是不是运动神经元病(即渐冻症)。”
确诊渐冻症等于“判刑”?樊东升不愿意用这个词。
身为北医三院神经科主任,樊东升是国内最早开始渐冻症研究的医学专家之一。和患者说话时,他的声音很轻,语速不快,问得很细: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利鲁唑有没有吃?体重有没有降?……一项一项,他都要问清楚、讲清楚。

2019年,在北医三院的诊室里,樊东升在给患者看病。
“不是所有的患者起病后都进展很快,在不欺骗患者的前提下,也要把他病情里的‘优势’讲出来,让他有活下去的渴望。”樊东升在神经科待了30多年,亲眼看见渐冻症的神秘面纱被缓缓揭开一角,从湮没无音到广为人知。他相信,会有闪烁的光点划破暗夜,而活着,就有希望。
“冷水”沸腾了
如果说自1869年渐冻症被提出并命名的一个半世纪以来,做渐冻症研究是身处一池“冷水”,那么,樊东升明显感觉到,眼下这水正在变得沸腾。
最直观的例子是相关学术会议的参会人员。从2004年中国ALS(肌萎缩侧索硬化,即渐冻症的英文缩写)协作组成立以来,樊东升参加了数不清的学术会议。“参会的都是临床医生,医生之间无非是交流旧有经验,但在科学层面的治疗,还是得等着国际上的新药研究出来,因为我们的药物研发能力不够。”医生们自说自话,说完就走了。
但2023年,樊东升惊喜地发现,参会人员里,超过一半是做渐冻症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会议开了整整两天,少有人提前离会,都在等最后的“重磅发言”——那可能是一个新的实验、新的发现、新的假说,将带来攻克渐冻症的新希望。
“甚至,很多科学家是‘转行’过来的。”
樊东升举了几个例子,西湖大学付向东教授、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李晓江教授、清华大学鲁白教授,等等。他们原本专注于帕金森病或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现在也都研究渐冻症。“渐冻症跟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有共通性,都是神经退行性疾病,但相比之下,渐冻症是研究神经退行机制更好的模型。因为它发展快,一天之内可能就变化了,科学家进行干预更容易看出研究有效与否。”
樊东升打心底里觉得:“人越多力量越大,不同科学家研究不同的方向,你觉得没希望了,说不定别人的方向上又冒出来一个希望。”而回头看,搅动这池“冷水”的,反而是一名病人——蔡磊。
北医三院健康医学中心,7层,每一个来面诊的人都拿着厚厚一摞资料,资料袋外印着天南海北的医院名字。2019年9月30日,同样的地点,樊东升第一次看到蔡磊耷下的左臂,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词是“连枷臂综合征”(渐冻症的临床变异型之一)。在2013年到2017年底,北医三院注册登记的3000多名渐冻症患者中,连枷臂综合征患者的病情进展最慢,平均生存时间在7—8年,有的患者生存了十几年,远远好于渐冻症患者的整体水平。
“确诊时,蔡磊的右上肢还没问题,病情比较乐观,10年以上没问题。”当时樊东升叮嘱蔡磊,好好调理,不要太拼。
樊东升记得,蔡磊看起来“对病情不是特别关注”,他的表情波澜不惊,没有太大变化,甚至小小的门诊室成了他谈笑风生的场地。
后来在书里,蔡磊回忆这一天:从樊东升的门诊室出来后,他等了两三趟电梯都没能进去,不想再等,拉着母亲去走楼梯。走出医院,他手脚冰凉,“电梯都不愿意等,现在却只能等死”。诸如此类意志消沉的一面,樊东升没有看到。
确诊后不到一个月,蔡磊又找上了他,说想做一个渐冻症患者的大数据平台。樊东升答应了他。早在2000年初,樊东升就有过类似的想法。
当时还没有电脑系统,病例手写完毕,患者就带回家了,医院也没有留底。等到他想了解患者的诊断数据、病情进程、用药情况时,只觉得两眼一抹黑。樊东升就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帮他设计了一套量表,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渐冻症患者的资料。“这边医生写完病历,患者签了‘知情同意’,那边科研护士抓紧时间誊写建档。”
到2019年,北医三院已经收集了5000多名渐冻症患者的数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样本库。但这些数据还不够动态,有的患者3个月后还能跟访到,有的就彻底失去联系了。“蔡磊想搭建的是一套病人自报系统,可以持续追踪。他很会利用互联网,我们给他专业上的建议,他去搭建这个平台,一两年间就有上万人填写。”樊东升说,这个样本量是过去20年间收集数据的两倍——确实是只有蔡磊这样兼具互联网“大厂”高管和渐冻症患者双重身份的人才能做到的一个数据。

2022年,樊东升(右)参加一档电视节目,在节目中遇到了蔡磊。
再之后,樊东升常常听到蔡磊“爱折腾”的其他消息:疯狂拉企业家投资渐冻症新药研发,不停地找科学家推新的药物管线,在社交群里呼吁患者捐献遗体给医学研究用……
折腾的成果让樊东升动容:“1000多名患者签署了遗体捐献同意书,这不亚于‘冰桶挑战’的贡献。”2014年,“冰桶挑战”公益行动风靡全球,美国筹到的1.15亿美元善款中,7700万美元用于研制渐冻症的治疗方案;中国共筹到814万元人民币,550多万元用于帮助渐冻症患者群体,剩下250多万元用于帮助其他罕见病群体。在樊东升看来,蔡磊动员到1000多名渐冻症患者同意捐献遗体,是实实在在把渐冻症的研究进展往前拨动了很多格。
折腾的后果也让樊东升心里一凉。樊东升再见到蔡磊时,“他告诉我,不光右胳膊动不了,脖子也开始没劲儿。这个症状在他身上出现得太早了。从上肢到脖子,意味着病情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很多病人,两个胳膊动不了,但脖子没事,说话、走路如常,这样的状态可以持续七八年。但他太拼了,不听医生的话”。渐冻症患者的神经细胞没有正常的“应激颗粒”守卫,一碰到过度劳累等应激状态,无异于“赤手搏击”,很容易损害甚至死亡。
樊东升只好又一次叮嘱他:“一定要小心,别太拼。”
蔡磊说:“知道。”
蔡磊的折腾其实赶上了时代的大潮。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樊东升在临床一线,深刻地体会到,正是有了“健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大环境,罕见病治疗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包括渐冻症新药的引进、试验、评审等,都可以走绿色通道,加速进行。“恰在此时,有蔡磊这样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出来呼吁。”
“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不一样。你老老实实在那待着,可能多活10年,但不会有这么大的动静。”樊东升尊重蔡磊的选择。2023年7月,樊东升和中国科学院药物所高召兵教授、清华大学贾怡昌教授联合研究团队在国际高水平科学期刊《自然》(Nature)杂志子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上发表封面文章,介绍渐冻症研究的最新发现。樊东升和贾怡昌一致建议,杂志封面采用蔡磊的个人照。

樊东升请人设计的《细胞研究》封面。
为此,他们专门请了美术设计。封面背景是一片未知的荒漠,蔡磊仰着头,太阳光洒下来,空气中有飘起来的泡泡,有象征他们新发现的致病基因的元素符号。“想以此来致敬他身为一名患者作出的贡献。”
这款封面最终未被采用,樊东升有点遗憾:“我们——医生、患者和研究人员——其实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渐冻症。”
找到那把“钥匙”
对面是一名来自山东的女性患者,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开了,又不甘心地问樊东升:
“樊医生,你们的新药进临床了吗?我想进组(试验)。”
她的眼眶红了,她说自己也是一名医生,现在吃不下,也睡不着。
这不是樊东升第一次遇见这种场景,他尽力劝慰对方:“维持营养和体重是基本的,你要是吃不好睡不好,没病也该病了。”
渐冻症对每个患者都是平等的。在樊东升的门诊室,更能体会这一点。他们可能很年轻——系统叫号喊“蔡磊”,众人纷纷探头,一个同名的27岁小伙子进了诊室。他的姨妈几年前确诊了渐冻症,他不相信“诅咒”这么快就降临到了自己身上,用含混却坚定的声音跟樊东升说:“我来,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渐冻症。”他们可能是高知——在其他人时刻维持着“冲”进诊室的姿势时,一对打扮很体面的夫妻静静地靠在椅背上。丈夫的手里攥着一张纸,纸上列了五六个问题,字体舒朗飘逸。
起初,每一名渐冻症患者都会感到恐慌、焦虑、不知所措,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身体一寸一寸被“冻”住,一寸一寸失去力气和功能,而自己的脑子始终清醒。为什么会这样?
医生也回答不了。渐冻症患者中,除了5%—10%由基因突变导致,是父母遗传给孩子的,其余90%—95%都是散发性的,病因不明,靶点不清。这就好比是:想要攻敌,却连敌人在哪儿都摸不清。因此网上不乏一种声音:这种医生最好做,反正治不好。
樊东升也反问自己:我能做什么?我要做什么?
樊东升的祖父、父亲都是医生。当年他考大学,父亲自然而然就替他选了医学专业。1984年,樊东升从第三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医疗系毕业。全系204人,有被分配到西藏的、海岛的和战斗一线的,他则被分到学校附属医院新桥医院(现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选神经内科,是因为他觉得“逻辑性强,80年代医院的检查设备很少,脑子里病变在哪儿?基本上靠医生查体推论”,他想象那是一件“很烧脑、很酷”的事情。
干了一段时间后,樊东升不这么看了,“当时对脑血管病都没有办法,连溶栓治疗都没有,神经免疫类疾病的治疗更是只有‘三大素’(激素、抗生素、维生素),医生更多是诊断,诊断完了,没有治疗。”
1987年,北医三院神经内科开始向全国招收硕士研究生,樊东升成为第一批入读学生之一。当时整个神经内科只有12张床位,且没有独立的护理单元,但他仍忍不住感到激动、好奇——科里引入丹麦一家公司的新型肌电图机不久,在肌电图检查技术上全国领先,导师康德瑄则专注于临床电生理、神经肌肉病,方向很新。
正是在这里,樊东升学到了人生中重要的一课——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南长征,北三院”,说的是骨科治疗并驾齐驱的两大医院。来北医三院骨科看颈椎病的人特别多。一次闲聊,一名骨科医生和康德瑄说:明明手术做得很漂亮,我们颈椎病人,怎么一做完手术就进你们神经内科了?话一说完,双方心里都“咯噔”一下:这事儿,得会诊。结果发现,有的患者不是颈椎病,而是渐冻症。两种疾病都会出现肌萎缩,上肢、下肢麻木僵硬,导致一种罕见病被误诊为常见的颈椎病。也因此,做完颈椎手术的病人出现了说话不清、吞咽困难的症状。
如何区分颈椎病和渐冻症?当时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诊断标准。“哪儿没劲,就给哪儿做肌电图。”樊东升伸出手比划:“一做肌电图,电极贴满整条胳膊,检查十几块肌肉,完全是抓瞎。”在导师的建议下,他开始寻找线索。他跑遍全北京市的图书馆,终于发现了一篇以色列文献。文中提到通过胸段的椎旁肌进行区分,因为得了颈椎病的人胸段很少出现退行性病变。
这点醒了樊东升。但胸段病变是渐冻症患者比较晚期的症状,他想找出早期就能区分两种疾病的方法。沿着前人的路线,樊东升想到颈椎病也不会影响脖子上的胸锁乳突肌,而同一部位,渐冻症患者的肌电图会有明显反应。
“钥匙”就这样找到了!
那是樊东升极具成就感的一刻,也是中国渐冻症医治史上重要的一刻——通过胸锁乳突肌诊断的准确率达到98%以上,这一方法被纳入中国渐冻症诊断标准。
绝望和希望
和樊东升多聊一会儿,就会发现他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清冷、疏离。相反,他心思细腻,对于患者的反应很敏感。
这种敏感源于他的同理心。前段时间,樊东升自己接受了心脏射频消融手术。躺在病床上干瞅着天花板时,他才发现一天见不到几次主治医生,见得更多的是临床护士。“这时医生多跟我说两三句,我就清楚很多,很受鼓舞。”
推己及人,樊东升觉得,最基本的,他有责任让患者正确认识渐冻症。早些年,他见过特别多为了治病而被骗的人,比如不少人相信吃生泥鳅可以治好渐冻症。现在,他的社交平台每天还能收到大量所谓的“偏方秘方”。甚至有人直接到医院堵住他,让他告诉自己蔡磊的住址,言之凿凿说有办法治好蔡磊的病。
“都是骗子,但还是有患者受骗。”樊东升理解这种心理:“人在得了一种不好的病时,总是希望有方法能彻底治好自己。”
但“治病”真的不等于“治好”。樊东升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患者和家属:“目前,渐冻症不能治愈,但可以延缓疾病的进程。”
利鲁唑是世界上最早治疗渐冻症的口服药物,已被证明延缓效果明显,“发达国家服用利鲁唑的比例达99%,但国内患者的认知还不够,或者不舍得花钱”。樊东升就遇到过一个患者,起初还能自己坐火车来北京取药,服用利鲁唑一年后,他觉得好像没用,便没继续服了。结果,病情迅速恶化,半年后他就出不了门了。
人类和渐冻症的斗争漫长而无解,樊东升的想法是“与病共舞”。如果患者提前做好营养和呼吸管理,维持生命没有问题。当然,他的心里也始终酝酿着更大的希望:新药。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的治疗推进基本靠国外的药。药进来了,虽然让病人有了治疗可能,但也赚了中国市场不少钱。”樊东升说。以利鲁唑为例,2017年以前,一盒是4000多元,仅够服用28天。2017年,利鲁唑被纳入医保药品目录后,患者买一盒只需自付1413元,负担大为减轻。但对每一名病人,樊东升还是会细心询问一下他们的经济条件,但凡对方有一点面露难色,樊东升就明白了,开给他的是药效一样、价格便宜2/3的仿制药。
新药的问世都离不开临床的验证。业内有一句话流传广泛,“一款新药的研发平均要花10亿美元、10年时间”,其实这句话还缺了后半句——却是不到10%的成药率。根据动物实验研发出的新药,进入临床试验后,成功率很低,尤其是渐冻症、阿尔茨海默病这一类神经退行性疾病。用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主任章京的话说:“投入1万个药物,只有1个药能成功。”
面对失败,科学家会选择较劲,资本不会。2024年2月16日,一款被寄予厚望的渐冻症新药DNL788,在二期临床试验中失败了。樊东升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它的开拓者是华人科学家袁钧瑛教授,前期的论文内容很扎实,动物试验做得也很漂亮,结果临床试验一出来,服用新药和服用安慰剂的两组病人,效果没有差别。一夜之间,整条药物管线全部停掉。对药厂和投资人来说,再投资就是浪费钱。”
“但实际真的无效吗?”樊东升认为,不是的,“很可能是临床试验的设计出了问题。1个小鼠和10个小鼠只有数量的差别,但在临床上,1个病人和10个病人的差别太大了。渐冻症病人90%以上都是非遗传性的,发病基因各不相同,所以还要追问,新药无效,到底是对哪种亚型无效?有没有用了它却很有效的亚型呢?”
这时就凸显出临床研究的重要性了。“临床医生根据临床经验帮助科学家做好整体的临床试验设计,筛选出适合不同新药进行试验的亚型群体。”樊东升说,在此基础上,他和蔡磊建立的渐冻症患者大数据平台就显现出了它的价值——快速招募、筛选出目标病人。
一个例子或许能帮助人们理解这个大数据平台的了不起:鲁白教授曾在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启动了两款渐冻症新药,都因参与试验的患者太少不了了之,“罕见病的临床试验人数要求至少是160—200例,一直收不满,拖一天就多一天的投入,最后被迫停止”。
而眼下,樊东升全程参与临床研究的渐冻症新药SNUG01,即将进入临床试验。新药的基础研究是贾怡昌教授团队做的,参与临床试验的人数也不用担心。但可以想象,进入临床试验,人类将又一次徘徊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或许,上一秒还是重生的狂喜,下一秒就是失败的深渊。

2023年,樊东升(前排左三)和清华大学贾怡昌(前排左四)团队开启渐冻症新药SNUG01的临床研究。
樊东升也在期待着。在这次大规模临床试验前,去年5月,应一名病情较重的患者强烈要求,他们为他进行了“同情给药”,先给他用上了SNUG01。一年里,樊东升亲眼看到他的肌电生理监测有了可喜的变化——原本几乎看不到起伏的直线,慢慢出现了电信号的曲线变化。那是樊东升看过的最美的图像!一位国内顶尖医生的坚持也就有了极其具体的意义:“人在,这个家就在。”(本文图片皆由受访者提供)

